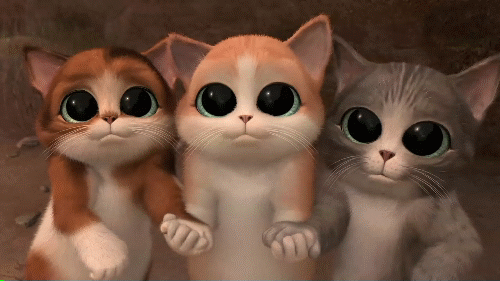战争对平民来说是血与死的代价,对权贵来说却是权与利的阶梯。
李长根,山东人,1950年入朝时才十九岁,隶属志愿军某师步兵连。那时候我们刚跨过鸭绿江,脚还没站稳,就被美军的飞机盯上了,天上轰隆隆的,像一群恶鬼在叫,白天不敢露头,只能晚上摸黑赶路,饿了就啃冻得硬邦邦的土豆,硬得牙都硌得生疼,渴了抓一把雪塞进嘴里,雪化成水时带着土腥味,咽下去像吞刀子,肚子咕咕叫也只能忍着。第一次上战场是在云山,11月初,天冷得手都握不住枪,风吹在脸上跟针扎似的,我记得那天晚上,山沟里全是炮声,震得耳朵嗡嗡响,空气里弥漫着硝烟和烧焦的味道,像地狱烧开了锅。我们连奉命冲一个高地,美军的机枪火力像泼水一样压过来,子弹嗖嗖地飞,身边的小张,十八岁的小伙子,刚喊了一句“冲啊”,就被子弹打中了胸口,血喷了我一脸,热乎乎的,黏在脸上抹都抹不掉,他倒下去的时候,眼睛还睁着,像在问我为啥不拉他一把,我吓得腿软,手抖得连枪都拿不稳,但还是跟着大部队往前爬。高地上全是尸体,有我们的,也有敌人的,踩上去软乎乎的,像踩在烂泥里,有的尸体被炸得只剩半截,手脚散了一地,血水混着泥淌成小溪,我鞋子陷进去,拔出来时全是红的。后来我被俘是在一次撤退中,部队被美军坦克截断了后路,隆隆的履带声碾得人心慌,我躲在石头后面,腿被炮弹碎片炸得血肉模糊,疼得我咬破了嘴唇,血腥味满嘴都是,动不了。美军士兵过来时,我以为要死了,手都摸向腰里的手榴弹想同归于尽,可手指冻僵了,拉不开栓,结果他们拿枪托砸了我脑袋一下,我就昏过去了。醒来时已经在战俘营,腿上的伤口已经发臭,蛆在里面爬,白花花的蠕动看得人头皮发麻,我疼得想喊,嗓子却哑了,喊不出声。营里吃的是一团团发霉的玉米面,硬得像石头,咬下去牙龈都出血,喝的是浑浊的水,有时候还有死老鼠漂在上面,恶心得人想吐又不敢吐。我见过一个战友,叫老王,为了抢一块玉米面团,被看守用刺刀捅穿了肚子,血流了一地,红得刺眼,他抓着那块面团,死都不松手,眼睛瞪得像要跳出来,死了还攥得死死的。战俘营里最怕的是审讯,美军会把人吊起来,用电棍捅你,电流窜过身体,像针扎进骨头缝里,逼你说部队番号和计划,我咬着牙不说,他们就拿烧红的铁条烫我胳膊,皮肉焦糊的味儿扑鼻而来,烫得我晕过去又被冷水泼醒,反反复复折腾。后来停战了,我被遣返回国,可腿废了,走路一瘸一拐,村里人看我的眼神都不对,像看个怪物,有的背地里说我当俘虏是叛徒,我也不敢说自己在战俘营的事,怕人骂我没骨气。直到老了,我还常梦见小张瞪着眼睛看我,血糊在他脸上,醒来一身冷汗,枕头都湿透了,心口像压了块石头,喘不上气。
赵福田,河北人,入朝时是炮兵连的观察员,负责在前线给后方报坐标,1951年春,我们在铁原附近布防,那地方山高坡陡,风一吹像刀子割脸,耳朵都冻得生疼,山上连棵遮风的树都没有,光秃秃的石头被炮弹炸得坑坑洼洼。战场上最吓人的不是枪炮,是美军的凝固汽油弹,那玩意儿扔下来,火一下子蹿起来,像红色的浪头扑过来,烧得人皮开肉绽,连骨头都能烧化,空气里全是焦肉味,熏得人喘不上气。我亲眼见过一个新兵,才十六岁,被烧得满地打滚,喊都喊不出声,嗓子被烧哑了,手在地上抓出一道道血痕,最后缩成一团黑炭,风一吹就散了,地上只剩一摊灰,连人形都看不出来。我们炮兵阵地经常被飞机轰,炸弹落下来,土和血一块飞,耳朵里全是“嗡嗡”声,分不清是炮响还是自己脑子坏了,有一次任务,我爬到山顶观察敌情,刚报完坐标,就被美军狙击手盯上了,子弹擦着我耳朵过去,耳朵当场聋了一半,血流下来糊住了半张脸,热得发烫。后来被俘是因为一次夜袭失败,我们连被包围了,炮弹把阵地炸得稀烂,炮管都被炸歪了,我被震晕在坑里,醒来时身边全是死人,胳膊上还压着一截断手,手指还攥着块石头,血已经冻成了冰碴子。美军把我拖走时,我身上全是血,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,衣服黏在身上,撕都撕不下来。战俘营里日子不是人过的,每天干活挖战壕,土硬得像铁,手磨得全是血泡,累得站不起来,看守还拿鞭子抽,抽一下皮就裂开,血渗出来冻在衣服上,疼得钻心。有个叫小刘的战友,饿得偷了看守的半块面包,被当场打断了腿,扔在营地门口冻了一夜,第二天早上人就僵了,脸上还挂着冰霜,眼睛半睁着,像在看天。我被俘后最怕的是“劝降”,有些被洗脑的战友劝我投降,说跟着美军有饭吃,我啐了他们一口,骂他们没骨头,结果被看守用枪托砸掉了两颗牙,嘴里全是血腥味,牙床疼了好几个月。停战后,我没回大陆,去了台湾,觉得自己没脸回去,怕家人戳脊梁骨。到了那边才发现,日子也好不到哪去,当兵的看不起我们这些“俘虏兵”,干活时总被指指点点,说我们是孬种,我后来在台北开了个小面摊,一个人过活,每天晚上关了摊子坐在小屋里,灯一晃就想起铁原那场大火,火光映在眼皮底下,觉得自己早该死在那儿了,活着反倒像受罪,夜里常被噩梦惊醒,手抖得连筷子都拿不住。
孙有财,东北人,1952年入朝时是机枪手,扛着一挺老式马克沁到处跑,那年秋天,我们在五圣山打阻击战,天上下着雨,地上全是泥浆,滑得站都站不稳,机枪架起来一打就歪,子弹打出去都偏了。我记得那天敌人的炮火特别猛,山头被削平了一半,石头和树全炸飞了,空气里全是硫磺味,呛得人喘不过气,山坡上全是弹坑,深得能埋下一个人,里面全是血水和碎肉。我的任务是守一个山口,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,刺刀断了就用石头砸,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,有个叫老杨的,肚子被炮弹炸开了,肠子流了一地,红白相间的,黏糊糊地挂在身上,他还抓着我的手让我别走,说怕疼,声音越来越小,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咽气,手上全是他的血,黏得洗都洗不掉。后来我被俘是因为弹尽粮绝,敌人冲上来时我还在装子弹,手指冻得根本动不了,被一个美国兵一脚踹翻,脸磕在石头上,牙掉了三颗,满嘴血腥味,头晕得天旋地转。战俘营里最惨的是冬天,帐篷漏风,风钻进来像刀子割肉,睡一觉起来身上全是霜,脚趾冻黑了,自己掰都掰不动,疼得钻心,吃的是更别提,一天就一小碗稀粥,里面漂着几粒米,饿得人眼睛发绿,胃里像有把刀在绞。我见过一个战友为了抢粥,把另一个战友的头按进泥里,俩人扭打成一团,结果都被看守用棍子打死了,尸体就扔在营地边上,乌鸦飞过来啄眼睛,黑乎乎的羽毛沾满了血。审讯时他们让我画部队地图,我不会画,手抖得连笔都握不住,他们就拿水管往我嘴里灌,水灌满肚子,胀得像要爆开,吐出来全是血丝,肚子疼得直不起腰。我熬到停战,被送回国,可家里人已经不认我了,说我当了俘虏是叛徒,连门都不让我进,我没地方去,就在山里搭了个窝棚,靠打猎过日子,风一吹就咳嗽,嗓子眼里全是血腥味。有一年冬天,雪太大,窝棚塌了,我被埋在里面,冻得迷迷糊糊,眼前全是五圣山上的血和泥,手脚都动不了,耳边好像还有老杨喊疼的声音,最后也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死了,意识模糊时只觉得冷得像掉进了冰窟。
张德全,河南人,1951年入朝时是卫生员,背着药箱到处跑,救人比打仗还忙。那年冬天,我们在长津湖附近作战,天冷得能把人冻成冰雕,风吹过来像鞭子抽脸,手伸出去不到一分钟就没知觉了,棉衣冻得硬邦邦,穿在身上像铁板。战场上到处是伤员,腿炸飞的,肚子破了的,喊声连成一片,我跑过去包扎,手指冻得拿不住纱布,血一沾上就结冰,红色的冰碴子挂在手上,像冻住的眼泪。我记得有个小战士,肚子被炮弹炸开了,肠子露出来,我给他塞回去,手上全是血和黏液,他疼得直抽搐,抓着我的胳膊喊“救我”,可我没麻药,只能眼看着他疼死,血流了一地,冻成一块红冰。后来被俘是因为一次转移伤员时,队伍被美军截住了,飞机在天上扔炸弹,地上全是火光,我背着一个伤员跑,腿被弹片划了个大口子,血淌了一路,伤员被炸死了,我也被震倒了,醒来时已经被绑在美军卡车上,腿上的血冻成了冰壳,疼得我直冒冷汗。战俘营里条件更糟,伤口没人管,发炎化脓,脓水顺着腿流下来,黄绿色的,臭得熏人,我自己拿石头砸烂了伤口,把脓挤出来,疼得满头大汗。吃的是一小块发黑的窝头,硬得像砖头,咬下去牙都疼,喝的水里全是泥沙,咽下去嗓子像被砂纸磨。营里有个老乡,叫小高,发烧烧得迷糊了,我给他擦身子降温,可没药,他还是死了,死时嘴里还喊着娘,眼睛没闭上,像在看我。我最怕的是看守拿伤员做试验,有一次他们抓了个伤重的战友,用刀在他腿上割,看他能活多久,血流了一地,那人喊得嗓子都破了,最后没气了,尸体被拖走喂狗。停战后,我回国了,可村里人说我当俘虏丢人,媳妇也跑了,我一个人住在破屋里,腿上的伤一到阴天就疼,疼得睡不着,晚上常想起长津湖的喊声,觉得自己没救下那些人,像欠了他们一辈子债,活着反倒成了负担。
王铁柱,山西人,1950年底入朝,是个炊事员,负责给部队做饭,可战场上哪有安稳做饭的地方。我们在汉江边扎营时,天天被炮弹轰,锅都被炸烂了,粮食也丢了一半,饿得战士们直骂娘。我记得有一次做饭,土豆刚煮上,美军飞机就来了,炸弹扔下来,锅炸飞了,土豆滚了一地,烫得我手上全是泡,我还得爬着去捡,身上全是泥和血。战场上最惨的是没吃的,前线打得凶,后勤跟不上,我们只能挖野菜,野菜吃多了拉肚子,拉出来全是绿水,肚子疼得直不起腰。后来被俘是因为一次运粮被伏击,车被炸翻了,我滚进沟里,腿摔断了,骨头戳出肉来,白森森的,疼得我满地打滚,美军过来时我爬都爬不动,被他们拖走了。战俘营里吃的更少,一天就一小块发霉的面团,饿得人眼睛发花,我见过两个战友为了一口面团打起来,一个把另一个掐死了,掐死后自己也疯了,整天抱着尸体哭。干活时得扛石头,腿疼得站不住,看守拿鞭子抽,抽得背上全是血道子,血干了黏在衣服上,脱下来皮都撕掉一块。最怕的是晚上,营地旁有狼嚎,饿极了的狼会跑进来咬人,有个战友半夜被咬掉了半张脸,血肉模糊地喊救命,没人敢过去,第二天早上只剩一堆骨头。审讯时他们让我说粮食藏哪,我不说,他们拿烙铁烫我胸口,皮烧焦了,疼得我晕过去,醒来身上全是汗和血。停战后,我回了山西,可腿断了干不了活,家里人嫌我是个累赘,我只能靠要饭过日子,拄着棍子走街串巷,晚上睡在桥洞里,风一吹就想起汉江边的炮声,觉得自己活着跟死了没啥两样,日子过得像嚼蜡,没滋味也没盼头。
陈大山,四川人,1951年入朝时是步兵连的班长,带着十几个兄弟冲锋陷阵。那年夏天,我们在金城附近作战,天热得像蒸笼,汗水流下来黏在身上,衣服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,身上全是盐霜,痒得抓出血来。战场上最怕的是美军的炮击,炮弹落下来,地动山摇,身边的土被炸得飞起来,像下雨一样砸在头上,我见过一个兄弟被炮弹炸得只剩半边身子,血喷得老高,掉下来时还烫手,空气里全是血腥味和土味混在一起的怪味。被俘是因为一次夜战,我们连被包围了,子弹打光了,我拿刺刀跟敌人拼,刺中一个美国兵,他血喷了我一身,我也被他同伴用枪托砸晕了,醒来时已经在战俘营,手腕被铁丝绑得血肉模糊,疼得钻心。营里日子苦得没法说,每天干活搬石头,手磨得全是血泡,破了又结痂,结痂又磨破,吃饭是一小块发霉的窝头,饿得人直吞口水,有个战友抢食被看守用棍子打断了胳膊,骨头断裂的声音清脆得像劈柴,他疼得满地滚也没人管。审讯时他们让我说部队番号,我咬牙不说,他们拿冷水泼我,再用电棍电,电得我浑身抽搐,牙齿咬破了舌头,满嘴血腥味。停战后,我没回大陆,去了台湾,觉得回去了也没脸见人。到了台湾,我被编进部队,可那些本地兵看不起我们,骂我们是“投降兵”,干活时总被使唤来使唤去,后来我退了伍,在高雄摆了个修鞋摊,一个人过日子,晚上常梦见金城那场炮击,醒来时手还攥着拳头,像要抓什么,摊子生意不好,日子过得紧巴巴,心里的苦谁也不知道。
刘二宝,湖南人,1952年入朝时是通讯兵,负责拉电话线跑前跑后。那年春,我们在上甘岭作战,山上全是石头和弹坑,跑起来脚底全是血泡,天天被炮弹炸得头晕眼花,空气里全是硝烟味,呛得嗓子像着了火。战场上最惨的是信号断了,电话线被炸断了我得爬出去接,子弹嗖嗖地飞,有一次我刚接好线,身边一个战友被狙击手打中了头,脑浆溅了我一身,白花花的黏在衣服上,我抖都抖不下来。被俘是因为一次送信,半路被美军截住,我跑不动了,腿被机枪扫中,血流了一地,疼得我满头冷汗,他们把我拖走时我还抓着信,死都不松手。战俘营里日子像地狱,每天挖土干活,腿上的伤口化脓,脓水流下来臭得熏人,吃的是一小碗稀粥,饿得人直打晃,有个战友偷了看守的半块饼,被当场打瞎了一只眼,血流下来糊住了脸。审讯时他们让我说部队位置,我不说,他们拿针扎我手指,扎得血肉模糊,疼得我晕过去又被泼醒。停战后,我去了台湾,怕回大陆被骂叛徒,到了那边干过苦力,后来在台中开了个小杂货铺,生意冷清,日子过得紧巴巴,晚上常想起上甘岭的硝烟,觉得自己像断了线的风筝,飘到哪算哪,心里的根早就没了。
我叫马永福,陕西人,1951年入朝时是迫击炮手,扛着炮管到处跑。那年秋天,我们在汉城附近打阻击战,天上下着雨,地上全是泥浆,炮架子陷进去拔都拔不出来,炮弹打出去声音震得耳朵疼。战场上最怕的是敌人的坦克,履带碾过来,地都抖,我见过一个战友被坦克压过去,血肉模糊成一摊,骨头碾得嘎吱响,血水混着泥淌了一地。被俘是因为一次阵地失守,炮弹打光了,我被爆炸震倒,耳朵流血听不见声音,美军冲上来时我爬都爬不动,被拖走了。战俘营里苦得没法说,每天扛木头,手磨得全是血,吃的是一小块发霉的面团,饿得人眼睛发绿,有个战友为了抢吃的被看守用刺刀捅死了,血喷了一地,尸体扔在营地边上没人管。审讯时他们让我画阵地图,我不会画,他们拿烙铁烫我背,皮烧焦了,疼得我满地打滚。停战后,我去了台湾,觉得回不去老家,到了那边当过建筑工,后来在台南开了个小饭馆,生意不好不坏,日子凑合着过,晚上常想起汉城那场雨,觉得自己像被炮弹炸散了魂,活着也没啥意思。
我叫周长生,江苏人,1950年入朝时是侦察兵,负责摸敌情跑山路。那年冬天,我们在长津湖附近侦察,天冷得手脚都冻僵了,风吹过来像刀子割脸,鞋子冻在脚上脱不下来。战场上最怕的是美军的飞机,轰隆隆扔炸弹,我见过一个战友被炸得飞起来,掉下来时只剩半截身子,血洒了一地,冻得硬邦邦。被俘是因为一次任务暴露,我跑山路时摔断了腿,骨头戳出肉来,疼得我满头冷汗,美军追上来时我躲在石头后面,还是被抓了。战俘营里日子不是人过的,每天挖战壕,手磨得全是血泡,吃的是一小块发黑的窝头,饿得人直晃,有个战友偷了看守的饭,被打得满脸是血,扔在营地门口冻死了。审讯时他们让我说出侦察路线,我不说,他们拿冷水泼我,再用电棍电,电得我牙关咬出血。停战后,我去了台湾,怕回大陆没脸见人,到了那边干过码头工,后来在基隆摆了个水果摊,日子过得紧巴巴,晚上常想起长津湖的雪,觉得自己像冻在冰里的鱼,动不了也活不透。
徐有根,浙江人,1952年入朝时是掷弹手,负责扔手榴弹炸敌阵。那年夏,我们在平康作战,天热得汗流不停,衣服黏在身上,战场上全是硝烟和血腥味,熏得人头晕。战场上最惨的是近战,我扔手榴弹时被敌人机枪扫中胳膊,血流了一地,疼得我满地滚,后来阵地被冲垮,我被俘了,美军拖我走时我胳膊还滴着血,疼得昏过去。战俘营里每天干活扛石头,胳膊上的伤口化脓,脓水流下来臭得熏人,吃的是一小碗稀粥,饿得人眼睛发花,有个战友抢食被看守用枪托砸死了,脑浆流了一地。审讯时他们让我说部队计划,我不说,他们拿鞭子抽我,抽得背上全是血道子。停战后,我去了台湾,觉得回不去老家,到了那边当过渔民,后来在花莲开了个小茶肆,生意清淡,日子过得平平淡淡,晚上常想起平康的硝烟,觉得自己像被炸散的魂,聚不回来。
根据美军统计,朝鲜战争期间,联合国军阵亡约36,574人,受伤约103,284人,失踪和被俘约8,177人;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亡人数估计在40万至60万之间,受伤人数更多,具体数据因统计口径不同而有争议。这些冰冷的数字背后,是无数个像上述俘虏一样的生命,在战火中挣扎、破碎,最终湮没于历史的长河。
赞(38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