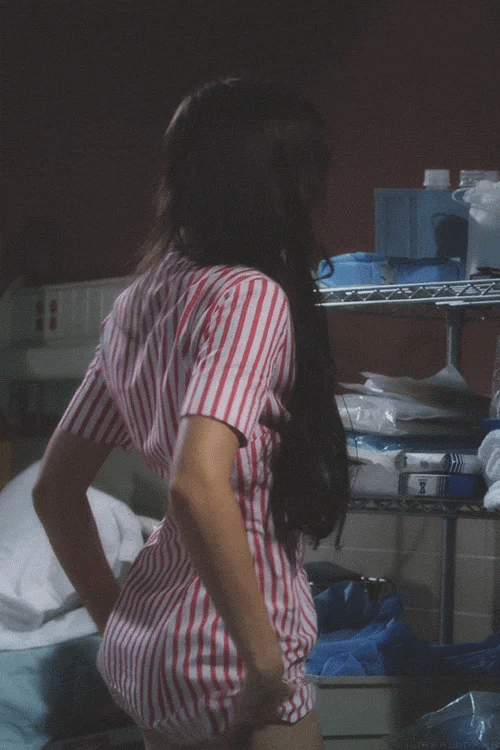1975年8月8日凌晨,板桥水库溃坝,洪水像脱缰的野马,吞没了驻马店的村庄和县城。洪水退去,留下的是一片废墟和无尽的悲痛。
魏长河,38岁,家住遂平县文城公社魏湾大队。那天晚上,天黑得像泼了墨,雨下得像天漏了底。我刚喂完牛,站在院子里抽一口旱烟,烟还没点着,雨水就顺着帽檐灌进脖子里,凉得我一哆嗦。老婆在屋里喊:“快进来,孩子怕!”我回头一看,三个闺女挤在炕上,大的12岁,拉着两个小的,眼睛瞪得像铜铃。突然,一声闷响,像是山炸开了,我还没反应过来,水就从西南方向扑过来,像堵黑墙。我一把抱起两个小的,手里拉着大的往大队部跑,那儿地势高。刚进院子,水头从墙上翻进来,像盖被子似的把人闷住。我被冲倒,水里全是泥和草,呛得我喘不上气。一个浪打过来,我手一松,两个小的没了。我抓着大闺女,死命往树上爬,水退时,她挂在树杈上,脸青得像纸,手还攥着我的衣角。家里6口人,4个没了,老婆和老二被冲到几十里外,捞上来时身上裹满烂泥,连脸都认不下了。
邓玉成,42岁,是遂平县城南街的木匠。那天夜里,我刚从县城回来,扛着一捆木料,雨水打在脸上,像针扎。街上静得出奇,只有雨砸地上的啪啪声。我推开家门,老娘在灶前烧火,锅里煮着玉米糊,热气腾腾。忽然,地抖了一下,像有人在地下敲鼓,我以为是错觉,可紧接着一声巨响,像是天塌了。我冲到门口,水已经漫过门槛,黑乎乎的,夹着树枝和破家具。我喊:“娘,快跑!”她拄着拐杖刚迈一步,水就涌进来,齐腰深。我背起她往高处跑,可水涨得太快,像野兽追着咬。我脚下一滑,摔进水里,老娘从背上掉下去,我抓了一把,只摸到她的拐杖。水退后,我在街角找到她,脸埋在泥里,身上压着一块门板,手里还攥着块玉米饼,像要递给我。
李桂兰,29岁,家在泌阳县林庄村,离板桥水库不远。那天晚上,我在屋里哄两岁的儿子睡觉,雨打在窗户上,像有人拿石头砸。我男人出去看水库,说是水位高得吓人。我刚把孩子哄睡着,门砰地被撞开,他满身泥水冲进来喊:“快跑,水库塌了!”我抱起孩子就往外冲,脚刚踩到院子里,水就到了膝盖,黑得像墨汁,臭得像死鱼。我男人拉着我往山坡上跑,可水来得太快,像张大嘴吞过来。我脚下一滑,孩子从怀里掉出去,我扑过去捞,只抓到他的小鞋子。水退时,我在村口的大树下找到他,小身子卡在树根里,脸朝下,嘴里塞满泥。我男人后来被冲到下游,挂在一根电线杆上,腿断了,活下来了,可他再也没说过一句话。
张世兴,35岁,是文城公社魏湾大队的民兵。那天夜里,我在队部值班,雨下得耳朵都嗡嗡响。队长让我去查河边的水情,我打着手电往外走,风把雨吹得横着飞,手电光只能照出几步远。走到河边,水已经漫过堤坝,像煮开了锅。我跑回队部,刚进门,水就冲进来,像堵墙砸在身上。我抓着桌子往房顶爬,水里漂着粮食袋和死鸡,臭得熏人。我喊老爹老娘上树,可水来得太猛,我刚把绳子系到屋檐上,水头就扑进来,绳子像线似的断了。我眼睁睁看着他们被冲走,老爹还挥了一下手,像在跟我告别。水退后,我在下游找到他们的尸体,老娘抱着一块木板,老爹手里攥着根烟袋,脸朝天,像睡着了。
吴桂兰,50岁,也是魏湾大队的村民。那天晚上,我跟11岁的闺女在炕上纳鞋底,雨水从屋顶漏下来,滴在炕上,啪啪响。我刚起身想拿盆接水,地抖了一下,紧接着水就从门缝挤进来,像活物似的。我拉着闺女往外跑,刚到院子,水头扑过来,像盖子扣下来。我俩被闷住,头顶的墙塌了,砸在我背上,疼得我眼前发黑。一个浪打过来,把我们掀出去,我抓着一张破席子漂了半夜,闺女却没了。水退时,我在河边找到她,小身子缠在芦苇丛里,手里还攥着那块鞋底,针扎在手指上,血干成了黑块。我背上的骨头裂了,走路一瘸一拐,可我宁愿那块墙砸死我。
陈大柱,47岁,是板桥水库附近的农民。那天夜里,我被雨声吵醒,爬起来看院子里的猪圈,水已经漫到猪肚子上了。我穿上蓑衣,拿根棍子去赶猪,雨水打在脸上,像鞭子抽。忽然,一声巨响,像炸雷,我回头一看,水库的方向黑压压一片,水头高得像山。我扔下棍子就跑,可水追得太快,像狼撵羊。我爬上一棵老槐树,水漫到树腰,猪圈里的猪嚎着被冲走,撞在树干上,血染红了水面。我在树上挂了一夜,手抓着树皮,抠出血来。天亮时,水退了,我下去一看,家没了,媳妇和两个儿子被埋在泥里,炕上的被子还盖在他们身上,像睡着了。
赵小英,19岁,是遂平县城的小学老师。那天夜里,我在学校值班,雨下得窗户都哗哗响。我裹着毯子坐在办公室,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,光晃得影子乱跳。突然,地抖了一下,灯摔在地上,火苗蹿起来。我冲到门口,水已经漫过操场,像黑色的毯子铺过来。我跑回教室,想叫醒寄宿的学生,可水来得太快,门刚开,水就涌进来,齐胸深。我抓着两个孩子往房顶爬,水里漂着课本和板凳,砸在我腿上。天亮时,救援队把我拉下来,两个孩子没撑住,一个被冲走,一个冻死在我怀里,小手还抓着我的袖子,硬得像木头。
王福田,53岁,是泌阳县马谷田镇的渔民。那天晚上,我在河边收网,雨水打得网都沉了下去,鱼在水里乱蹦。我穿着破雨衣,脚踩在泥里,冷得发抖。忽然,水面抖了一下,像被什么东西掀起来,我以为是大鱼撞网,可紧接着一声巨响,水从上游扑下来,像堵墙压过来。我扔下网往岸上跑,可水追得太快,卷着泥沙和树枝,把我拍进河里。我抓着一根浮木漂了半夜,水里全是死鱼和烂木头,臭得我直吐。天亮时,我被冲到岸边,爬上来一看,村子没了,媳妇和老娘被埋在屋里,捞上来时身上裹着鱼网,像被水怪拖走似的。
刘秀梅,26岁,是文城公社的一名赤脚医生。那天夜里,我在卫生室给人看病,桌上放着药瓶和纱布,煤油灯晃得影子乱动。雨下得窗户都模糊了,病人是个老汉,咳得喘不上气。我刚给他包好药,地抖了一下,紧接着水从门底下涌进来,黑乎乎的,像墨泼进来。我拉着老汉往外跑,可水涨得太快,齐腰深。我把他推到桌子上去,自己踩着凳子往房梁爬,水里漂着药瓶和破布,砸在我身上。一个浪打过来,桌子翻了,老汉掉进水里,我扑过去捞,只抓到他的草帽。水退后,我在门口找到他,脸埋在泥里,嘴里塞满纱布,像被呛死的。
孙大牛,31岁,是遂平县城郊的菜农。那天晚上,我在菜地里搭棚子,雨水顺着棚顶流下来,像瀑布。我穿着蓑衣,拿铁锹挖排水沟,泥水糊满裤腿。忽然,一声闷响,像是天塌了,我抬头一看,水从北边扑过来,像黑龙翻滚。我扔下锹就跑,可水来得太快,像盖子扣下来。我被冲倒,抓着一捆白菜漂了半夜,水里全是泥和菜叶子,呛得我喘不上气。天亮时,我被挂在树上,爬下来一看,家没了,老婆和儿子被埋在泥里,捞上来时手里还攥着个烂萝卜,像要给我做饭。
周兰英,40岁,是泌阳县林庄村的妇女主任。那天夜里,我在村口开会,商量防汛的事,雨下得耳朵都嗡嗡响。会刚散,我打着伞往家走,风把伞吹得翻了面。忽然,水从上游冲下来,像堵墙砸过来,我被卷进水里,伞骨扎进我胳膊,血混着水流。我抓着一块木板漂了半夜,水里全是哭声和喊声,像鬼叫。天亮时,我被冲到岸边,爬上来一看,村子没了,男人和两个孩子被埋在屋里,捞上来时身上裹着破席子,脸朝下,像睡在泥里。
马金宝,45岁,是板桥水库下游的砖窑工。那天晚上,我在窑洞里烧砖,雨水从洞口灌进来,弄湿了柴火,烟熏得我直咳。忽然,地抖了一下,紧接着水从窑顶涌进来,像瀑布倒挂。我冲到门口,水已经齐胸深,夹着泥沙和砖头,砸在我身上。我抓着窑边的梯子往上爬,水涨得太快,像要把人吞下去。我爬到窑顶,水退时一看,窑塌了,媳妇和老娘被埋在里面,捞上来时身上裹满砖灰,手里还攥着块烧焦的柴,像要给我生火。
板桥水库的设计与建设始于1951年,是治淮工程的一部分,位于淮河支流汝河上游,库容4.89亿立方米。设计上由苏联专家协助,采用土石坝结构,坝高24.5米,长约2000米,被称为“铁壳坝”。然而,建设用料却问题重重。据事后调查,坝体主要使用黏土和砂石,质量参差不齐,部分地段偷工减料,黏土未充分压实,抗渗能力不足。溢洪道设计宽度仅为300米,远低于应对极端洪水的需求,且施工中钢筋用量不足,混凝土强度未达标。大坝建成后仅14个月便投入使用,未经充分检测,隐患早已埋下。
灾难前,预警并非全无。8月7日,受台风“尼娜”影响,驻马店地区连降暴雨,24小时降雨量达1060毫米,超过水库设计标准的千年一遇洪水。驻守水库的34450部队于当晚19时发出特急电报:“水位急速上升,离坝顶仅1.3米,情况危急!”然而,电报未获及时回应。7小时后,第二次电报请求动用飞机炸开副溢洪道泄洪,仍无果。政府高层据传正忙于政治活动,未予重视。8月8日零时40分,水位超过坝顶,洪水漫溢,6亿立方米水量以每秒7.81万立方米的流量倾泻而出,6小时内冲毁下游一切。
人员伤亡统计令人震惊。官方数据称,洪水直接死亡2.6万人,受灾人口1015万,房屋倒塌524万间,耕畜损失102万头,京广铁路中断16天,直接经济损失近百亿元。但民间和学者调查显示,真实数字远超此数。全国政协委员乔培新等人披露,洪水及后续饥荒、瘟疫导致死亡人数达23万,作家郑义估算为24万。受灾范围覆盖30个县市,1780万亩农田被淹,1100万人失去家园。死亡人数中,直接溺亡约10万,后续因缺粮和传染病死亡约14万,堪称世界最惨烈的水库溃坝灾难。
这场灾难的原因,既有天灾,也有致命的人祸。台风“尼娜”带来的超强降雨是导火索,但水库设计缺陷是根源。溢洪道容量不足、坝体用料低劣、施工质量粗糙,使其无法承受极端洪水。预警失灵与政府应对迟缓加剧了悲剧。事前缺乏有效预案,事中未及时泄洪或疏散,事后救援迟滞,导致损失扩大。政治挂帅下,专家意见被忽视,如水利专家黄万里曾警告治淮水库群风险,却未被采纳。板桥水库的溃坝,不仅是大自然的咆哮,更是人祸的血泪教训。
赞(26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