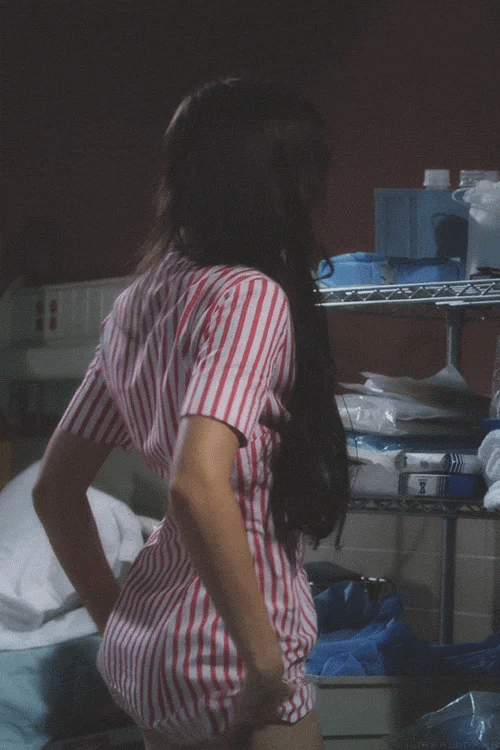2008年5月12日,下午2点28分,四川的天空还蓝着,阳光洒在山川田野间,像往常一样平静。可谁也没想到,大地会在那一刻撕裂,吞噬无数生命。
我叫汤明,27岁,家住四川什邡红白镇金河鳞矿厂宿舍楼。那天中午,我躺在四楼卧室的床上,迷迷糊糊地睡着。窗外阳光刺眼,风扇吱吱转着,远处传来狗叫声。我爸在旁边的厕所里,哼着小曲儿,估计是刚吃完饭在刷牙。突然,地面像被什么巨力拽了一下,我整个人从床上弹起来,还没反应过来,墙就裂开了,像被撕碎的纸。轰隆一声,整个楼塌了。我感觉自己像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搅拌机,耳边全是砖头砸地的闷响和金属扭曲的尖叫。我侧着身子摔在三楼的废墟里,左腿被一根钢筋死死卡住,血顺着裤腿往下淌,温热又黏稠。四周黑漆漆的,只有头顶一小块缝隙透进光,灰尘呛得我喘不过气。我喊:“爸!爸!”声音撞在废墟上,回音嗡嗡的,没人应。我听见远处有狗在嚎,撕心裂肺的那种,后来声音越来越弱,直到没了。我爸和那只狗,就在几米外,可我动不了,只能盯着那缝隙发呆。时间像凝固了,我不知道过了多久,嘴里满是土腥味,手指抠着地上的碎石,血和泥混在一起。40多个小时后,解放军空降兵把我挖出来,我才知道,爸没撑到那时候。他被压在厕所的门框下,手里还攥着牙刷,脸朝我这边,像是要说什么。
我叫刘红丽,17岁,是绵竹市汉旺镇东汽中学高二(1)班的学生。那天第二节课刚下课,我跟几个同学在教室里聊天,课桌上的书还摊着,上面画满了乱七八糟的涂鸦。窗外操场上有男生在踢球,尘土飞扬。突然,桌子开始抖,像有人在下面使劲踹。我还笑着说:“谁这么无聊?”可下一秒,地面像波浪一样翻滚起来,墙上的黑板哗啦一声掉下来,砸在第一排的课桌上。教室里尖叫声炸开了,有人往外跑,有人钻桌子底下。我愣在原地,腿软得像面条。这时,我们班主任张老师冲过来,他快50岁了,平时走路都慢吞吞的,可那会儿他像一阵风。他一把抓住我,把我往他怀里塞,然后扑倒在地,用背挡住我。头顶的天花板塌了,水泥块砸下来,我听见他闷哼一声,身上一沉。我被压在他身下,脸贴着地板,闻到一股浓烈的血腥味。他的手还抓着我的胳膊,越来越凉。我哭着喊:“老师!老师!”他没动。后来救援队把我挖出来,我才看到,他背上全是血,脊梁骨都露出来了,眼睛还睁着,像在盯着我。我舅舅后来跟记者说:“要不是张老师护着,这丫头活不了。”可我宁愿没活下来,那双眼睛老在我梦里晃。
我叫李小军,12岁,家在汶川县映秀镇。那天我在学校上体育课,操场上满是跑来跑去的同学,老师吹着哨子让我们排队。我穿着破球鞋,脚底的沙子硌得慌。天空蓝得晃眼,远处山上的树绿得发亮。突然,大地像被什么东西猛踩了一脚,我摔了个跟头,脸磕在地上,嘴里全是血和土。操场裂开了,像被刀劈出一道口子,旁边的教学楼晃了几下就塌了,尘土冲天而起,像蘑菇云。我爬起来就跑,可脚下像踩着棉花,跑不动。回头一看,同学小胖被一根掉下来的电线杆砸中,腿压在下面,血淌了一地,他抓着地上的草喊救命。我想过去拉他,可又一声巨响,教学楼的二楼整个砸下来,把他埋了。我吓得瘫在地上,耳朵里全是嗡嗡声,眼前的世界像蒙了层灰。远处山上滚下巨石,轰隆隆地砸进镇子,房子一栋接一栋倒塌,像推倒的积木。我妈后来找到我时,我还坐在操场边,鞋子丢了一只,手里攥着一把草,嘴里一直念:“小胖,小胖……”她抱着我哭,可我哭不出来,只觉得胸口堵得像要炸开。
我叫王芳,35岁,是北川县城一家小卖部的老板娘。那天我在店里算账,柜台上放着刚进的香烟和几瓶矿泉水,收音机里放着邓丽君的歌。店门口的塑料帘子被风吹得哗哗响,几个老顾客坐在门口嗑瓜子。地震来的时候,我正低头翻账本,桌子突然跳了一下,账本掉在地上。抬头一看,货架上的东西像瀑布一样往下砸,玻璃瓶摔碎了,汽水溅了我一身。我冲到门口,脚刚迈出去,房子就塌了,门框砸在我背上,我扑倒在地。街上的人尖叫着跑,尘土像雾一样罩下来,我看见对面卖菜的老张被一块飞来的水泥板砸中脑袋,血喷出来,像开了花。他倒下去时,手里还抓着个西红柿,滚到我脚边。我爬不起来,只能看着街上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埋。旁边一栋五层楼晃了几下,轰然倒塌,里面传出孩子的哭声,很快就没了。我被埋了十几个小时,救援队找到我时,我嘴里咬着一块碎布,满脸是血,背上的骨头断了三根。后来我听说,整个北川老城没了,我男人和儿子都没能爬出来。
我叫陈大爷,63岁,住在都江堰市聚源镇的一个老院子里。那天我在院子里晒太阳,躺在一把竹椅上,手里拿着一把蒲扇,扇得吱吱响。院子里的鸡咯咯叫着啄地,隔壁老李头在修自行车,叮叮当当的。地震来的时候,我先听到一声闷响,像远处炸山,然后地开始抖,竹椅直接翻了,我摔在地上,屁股撞得生疼。抬头一看,院墙裂了条大缝,砖头哗哗往下掉。我爬起来想跑,可腿抖得像筛糠。房子开始塌,瓦片像雨点一样砸下来,我眼睁睁看着老李头被一根房梁压住,头破了,血淌了一地。他瞪着眼睛看我,嘴里吐着血泡,想说话却没声。我扑过去想拉他,可房梁太重,我的手指抠进木头里,抠出血来也没用。远处传来轰隆声,我回头一看,整条街的房子都塌了,烟尘冲天,像世界末日。救援队把我挖出来时,我还抱着那根房梁,手上全是血口子。老李头的自行车散了一地,车铃被压扁了,还在叮叮响,像在跟我告别。
我叫张小红,9岁,是青川县木鱼镇小学的学生。那天我们在教室里上语文课,老师在黑板上写字,粉笔灰飘下来,弄得我鼻子痒痒的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,窗外有只麻雀在树上跳来跳去。突然,桌子抖了一下,我还以为是后桌的淘气包踢的,可紧接着地板像波浪一样翻起来,黑板裂成两半,老师手里的粉笔掉在地上。教室的墙塌了,我被甩到窗台上,玻璃碎了一地,扎进我胳膊里,疼得我哇哇哭。老师喊:“快跑!”可我刚站起来,屋顶就塌了,我被埋在课桌下,眼前一片黑,只能听见同学的哭声和尖叫声。桌子被压得吱吱响,我感觉有东西滴在我脸上,黏糊糊的,伸手一摸,是血。我吓得不敢动,嘴里喊着:“妈妈,妈妈……”也不知道过了多久,救援队把我挖出来,我才知道,滴在我脸上的血是老师的。她趴在我旁边的课桌上,头被一块水泥板砸穿了,手还伸向我,像要拉我一把。
我叫赵强,32岁,是汶川县威州镇一家小饭馆的老板。那天中午生意不好,我在后厨剁鸡,案板上的鸡肉还没切完,菜刀闪着寒光。窗外街上人来人往,摩托车突突响着,空气里飘着油烟味。地震来的时候,我正举着刀,地面猛地一晃,案板上的鸡肉滑到地上,刀差点砍到我手。我还没站稳,墙上的砖头就哗啦啦往下掉,灶台塌了,煤气罐滚到我脚边,嘶嘶漏气。我吓得魂飞魄散,冲到门口,可门框已经歪了,卡得死死的。屋顶塌下来,我扑到桌子底下,头顶的木梁砸下来,擦着我头皮过去,头发烧焦了一片。外面街上尖叫声不断,我听见隔壁卖水果的小刘喊:“救命!”声音刚起就断了。我被埋了整整两天,嘴里全是土,嗓子干得像要裂开。救援队找到我时,我还抓着那把菜刀,手指关节都白了。后来我才知道,小刘被一块掉下来的广告牌砸中,脑袋开了花,水果摊上的西瓜滚了一地,红瓤混着血,黏在地上。
我叫何秀兰,45岁,家住绵阳市平武县南坝镇。那天我在田里插秧,赤脚踩在泥水里,水凉得刺骨,秧苗绿油油地晃着。远处山上云雾缭绕,偶尔有鸟叫声。地震来的时候,我正弯着腰,地底下像有什么东西炸开,水田裂出一道口子,泥水喷了我一脸。我摔进田里,手里的秧苗散了一地。抬头一看,旁边的土坯房塌了,烟尘冲天,我男人还在屋里喂猪。我爬起来跑过去,脚被田里的石头划破,血顺着脚踝淌。到了屋门口,只剩一堆废墟,猪圈里的猪嚎着,被压得血肉模糊。我喊:“老李!老李!”嗓子喊哑了也没人应。我用手扒砖头,指甲裂了,血和泥糊在一起。远处山上滚下巨石,轰隆隆砸进村子,房子一栋接一栋倒。我扒了三个小时,手抖得拿不住东西,才摸到他的一只手,冷得像冰。我被救出来时,腿上全是血口子,救援的人说:“你男人没气了。”我坐在废墟边,看着那只手发呆,脑子里一片空。
我叫杨小龙,19岁,是都江堰市向峨乡中学的高三学生。那天我们在上数学课,教室里闷热,风扇吱吱转着,黑板上写满公式。我坐在最后一排,偷偷玩手机,屏幕上是一款赛车游戏。地震来的时候,手机掉在地上,屏幕裂了,教室的地板像被掀起来,我整个人摔到墙角。墙上的裂缝像蜘蛛网一样蔓延,课桌椅哗啦啦倒了一片。前面有个女生尖叫着往外跑,可门刚打开,屋顶就塌了,她被压在门框下,腿扭成怪样子,血淌了一地。我爬到窗边,想跳出去,可窗台也塌了,我挂在半空,手抓着窗框,下面是三楼的废墟。我听见楼下有人喊:“救我!”声音越来越弱。我挂了十多分钟,手指抠出血来,终于被消防员拉上去。回头一看,那个女生还压在门下,眼睛睁着,嘴里吐着粉红色的泡沫。我捡起地上的手机,屏幕还亮着,游戏里的车停在终点线上。
我叫马翠英,28岁,家在北川县擂鼓镇。我是个新手妈妈,那天我在家哄孩子,六个月大的儿子躺在摇篮里,咯咯笑着。窗外阳光洒进来,照得屋里暖洋洋的。我正给他换尿布,地震来了,地面像被什么东西猛踹了一脚,摇篮翻了,孩子摔在地上,哇哇大哭。我扑过去抱他,可墙塌了,砖头砸在我背上,我抱着他滚到床底下。屋顶塌下来,床板被压得吱吱响,我用手撑着,胳膊抖得像要断。孩子在我怀里哭,脸憋得通红,我闻到一股尿骚味,是他吓得尿了。我喊:“有人吗?救命!”可外面只有轰隆声和风声。我被埋了一天一夜,嗓子喊哑了,嘴里全是血腥味。救援队挖开废墟时,我还抱着孩子,他已经没气了,小手抓着我的衣服,硬邦邦的。我哭不出来,只觉得心被掏空了。
我叫周大成,51岁,是汶川县漩口镇的一名货车司机。那天我在镇上装货,车厢里堆满水泥袋,汗水滴在车板上,晒得滚烫。街上人声鼎沸,卖菜的吆喝声混着摩托车的轰鸣。地震来的时候,我刚爬上驾驶室,车子猛地一晃,像被什么东西顶起来。我摔出车门,脸磕在地上,牙掉了两颗。抬头一看,旁边的仓库塌了,水泥袋像雪崩一样滚下来,我爬起来就跑,可脚下像踩着浪,跑不动。身后一声巨响,车被埋了,油箱炸开,火光冲天。我回头看,仓库的老板老王被一块铁皮削了半个脑袋,血喷得像喷泉。我跑了几步,地裂开一条缝,我掉进去,腿卡在里面,疼得我咬破了舌头。救援队把我拉上来时,我满嘴是血,腿断了,只能看着那堆废墟发呆。老王的血干在地上,黑乎乎一片。
我叫邓丽,24岁,是绵竹市遵道镇卫生院的一名护士。那天我在给病人挂水,病房里满是消毒水味,窗外树影摇晃。地震来的时候,吊瓶晃得叮叮响,病人还没反应过来,墙就塌了,吊瓶砸在地上,玻璃碎了一地。我喊:“快跑!”可病房里都是老人和孩子,跑不动。我拉着一个瘸腿的老太太往外冲,门刚开,屋顶塌了,我被压在门边,腿卡在水泥块下。老太太摔在我旁边,头撞在墙角,血淌下来,染红了她的白头发。她抓着我的手,喘着气说:“丫头,别管我……”话没说完就没了声。我动不了,只能看着病房里的人一个接一个被埋,哭声喊声混在一起。我被埋了20多个小时,腿肿得像木头,救援队挖我出来时,老太太的手还抓着我,僵得像石头。
我叫罗小刚,15岁,是青川县关庄镇初中的学生。那天我们在操场上打篮球,球刚投出去,地就抖了一下,我摔了个狗啃泥,篮球滚到一边。操场裂开一条缝,教学楼晃了几下就塌了,尘土像雾一样罩下来。我跑向宿舍,想找我弟,可半路被一块掉下来的砖头砸中肩膀,疼得我眼前发黑。宿舍楼已经塌了,我弟在里面,我喊:“小明!小明!”嗓子喊出血来也没人应。我用手扒废墟,指甲断了,血滴在砖头上。远处山上滚下石头,砸进镇子,轰隆声震得我耳朵疼。救援队找到我时,我还扒着废墟,手上全是血口子。我弟被挖出来时,身上压着一张床板,小脸青紫,眼睛还睁着,像在看我。
我叫孙梅,39岁,家在什邡市洛水镇。那天我在家织毛衣,针线在手里穿来穿去,电视里放着广告,声音嗡嗡的。地震来的时候,电视机跳了一下,屏幕黑了,房子开始晃。我跑向门口,可地板裂开,我摔下去,腿卡在缝里。屋顶塌了,砖头砸在我头上,血流进眼睛,红蒙蒙一片。我男人冲过来,想拉我,可一根房梁砸下来,他被压在下面,胸口塌了,血从嘴里喷出来。我喊:“老公!”可他只喘了几口气就没了。我被埋了两天,头上的血干了,结成硬块。救援队把我挖出来时,我还抓着他的手,手指僵得掰不开。房子没了,毛衣针插在废墟里,线散了一地。
这场地震的伤亡数字令人触目惊心。据官方统计,截至2008年9月25日,汶川地震共造成69,227人遇难,17,923人失踪,374,643人受伤,直接经济损失约8451亿元人民币。学生群体的伤亡尤为惨重,因地震发生在白天上课时间,大量校舍倒塌。根据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的数据,至少有5335名学生遇难或失踪,受伤人数难以精确统计。仅在重灾区,就有超过7000所学校教室倒塌,其中包括北川中学、汉旺东汽中学、聚源中学等知名案例。北川中学约1000名师生被埋,汉旺东汽中学超过600名学生丧生,聚源中学近300名学生遇难。这些数字背后,是无数像刘红丽、李小军、张小红、杨小龙、罗小刚一样的孩子,他们的青春被永远定格在废墟下。
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办公设施的损毁情况。据调查,汶川地震中,北川县政府大楼、汶川县政府办公楼等部分设施虽有受损,但倒塌比例远低于学校建筑。例如,北川县老城几乎全毁,但新建的县政府大楼主体结构得以保留。都江堰市政府大楼虽有裂缝,却未完全垮塌。这种差异引发了公众对建筑质量的质疑,尤其是学校建筑为何如此脆弱。媒体和民间调查指出,许多校舍存在“豆腐渣工程”问题——偷工减料、钢筋不足、设计不合理。例如,北川中学的教学楼被曝出墙体厚度不足,钢筋细如铁丝,聚源中学的地基甚至未达抗震标准。
面对“豆腐渣工程”的指控,政府的态度复杂而矛盾。震后初期,官方迅速组织救援,投入大量人力物力,赢得了国际赞誉。然而,当家长和民间人士要求彻查校舍质量、追究责任时,政府反应趋于谨慎。2008年6月,四川省政府承诺调查建筑质量问题,但后续报告多以“地震强度超预期”为由,淡化人为责任。一些试图维权的家长被监控或劝阻,如北川中学遇难学生家长代表唐敏,曾多次上访要求追责,却被地方官员以“维护稳定”为由限制行动。2009年,官方发布《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》,强调重建优先,却未对责任人作出明确追责。学者指出,这种态度反映了政府在灾后重建与社会稳定间的权衡,避免因追责引发更大争议。
汶川地震不仅是自然灾难,更是人祸的缩影。那些倒塌的校舍,那些被埋葬的孩子,是建筑质量的沉默控诉。政府在救援中的果断与在追责中的暧昧,形成鲜明对比。十多年过去,废墟上的新城拔地而起,但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,仍在等待一个答案。
赞(27)